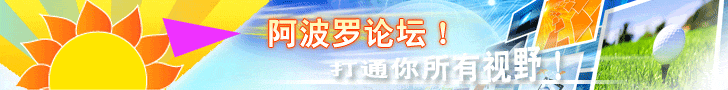方克立 (1938-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前院长(1994-2000),哲学家。 湖南省湘潭人,1938年6月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是知名历史学家方壮猷之子。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历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成员,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国际中国哲学学会驻大陆代表。80年代初期,他开创了新儒学的研究,完成国家"八五"社科规划的重点课题,成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的负责人,在海内外新儒学研究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个女人和她的遭遇 ——方克立两三件事
来哈佛读书前我曾经充任《华语华人报》的编辑。这份Job对于我来说主要是出于Money方面的考虑,因为我对于该报主要着眼于揭露秘闻丑闻奇闻的方向并不是很认同,而且该报的出版断断续续,给受雇人员某种不稳妥的感受。那时我已经发表了不短不长的处女作,内心里实际上有很多风花雪月的东西。可是,离开前最后参与编辑一个专栏的经历,却令我终生难忘。
专栏是关于女人和她们的遭遇。《华语华人报》都是采取当事人亲述,记者参与调查的方式。有人提供了一条线索,见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她眼神里的忧郁。她结过婚,很快就离异了,许多年来一直独居。从她那里我知道了方克立的名字。好多年前了,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学位,方克立是研究生院院长。"他这人表面看上去很平和,容易接近。"几次接触后,她阴差阳错地求他帮忙,然后就发生了那天晚上的事情,地点是研究生院招待所。
接下去我对于方克立有了更多的了解,知道他是研究中国哲学的,批判冯友兰起家的,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又是几个官方委员会的委员。在海外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北京大学的汤一介老先生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气愤地说:"方克立总是利用政治整人。"后来我知道,中国大陆有很多人听到这个采访,因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大约是境外的华语广播中收听率最高的。
可是专栏的那篇叙述却进展得并不顺利。首先是当事人的亲述遇到了问题。她总是断断续续犹犹豫豫,似乎必须割除某个毒瘤而又惧怕疼痛。"你能够确定那是强暴吗?""当然!你以为我那么贱吗?"她的眼神里闪过一束光亮。"那你犹豫什么呢?怕别人不相信吗?""没有女人会在这种事情上撒谎,我是怕-------""怕什么?""怕别人
认为那本来就是一种交易,就像很多人所从事的那样。毕竟他是院长,我只是一个学生。""你是说你后来确实从他那里得到了好处或者说是帮助?"她点了点头。"而且当时同学中就有风言风语什么的?"她又点了点头。"你想那是在研究生院招待所。你可以喊叫,或者是跑掉。""你是说,那说到底是属于某种胁迫的方式?"她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那么这些年来折磨你的是什么呢?""听起来可能有点荒唐。事情发生几天后,我发现自己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便威胁说要告发他。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他是坚持某某某主义的旗子,上边有人维护他。你说我成了什么了呢?"
这听起来确实有点荒唐,可是又不荒唐,我又想起汤一介先生说的:"方克立总是利用政治整人。"他也利用政治整女人。
有一次她对我说,她还知道两个相类似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她研究生院期间的两个同学。她讲述了那两位的故事,讲得具体而流畅。我说,这很重要,也非常有价值。问题是依据我们报纸的原则只有当事人亲述才能够采用,她们是否愿意公开自己的故事吗?她说,这恐怕有困难。她们都成了家,有了孩子,至少表面上看生活得还可以。我们多少次争执过,她们希望忘却或者说装作忘却,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那段屈辱的遭遇。我说,或许我可以直接和她们联络,看看是否有可能说服她们。她犹豫再三,最后给了我一个姓名和电话号码。电话号码是很远的一个城市的。我拨通电话,打招呼,说明我是从哪里得到的电话号码,然后自报家门,并说明我们正在做什么,问她是否愿意谈一点过去的事情,电话里谈或者是我飞过去都可以。对方悄无声息地挂断了电话,再拨过去电话没有人接听。
有时候她会变得很激进,说是要诉诸法律解决问题,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可是她能够提供方克立前胸的一个体征。接下去又说,这恐怕也行不通,听说方克立做了开胸手术,前胸的体征八成也已经破坏了。又有一次,她在电话里问我,方克立的家庭住宅就在附近,却又允许他长期占用招待所的一套房间,你说这是为什么呢?我没有明白她想搞清楚的是什么,只好反问:你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她没有回答。
那个夜晚成为一个魔咒,浸透了她,覆盖了她,控制了她。接触了几次以后,就连我都感受到那种难以摆脱的沉郁和压抑,仿佛自己从一个旁观者倾听者采访者被拖入了事件之中,与她一起经历或分担着什么,那些风花雪月的浪漫和轻狂消逝得无影无踪。有时候我为她感叹:一个可怜的女人!有时候我又为自己感叹:这是成熟吗?
她提供了几个姓名和电话号码。我收获最大的是联络到和方克立共事过的一位,当时他是研究生院的副院长。为了避开人们对于记者行业的警觉,我说自己在哈佛读书,正在研究意识形态背景下的人格特征。这倒也算不上是撒谎欺骗,我当时已经被哈佛大学录取,而且也确实对于"意识形态背景下的人格特征"具有浓厚的兴趣,这或多或少得力于参与《华语华人报》几个专栏的采访编辑。关于方克立,那位副院长说了一句骂人的话,言语间那种鄙夷和轻蔑令我吃惊。他说方克立是"一条专门在背后咬人的狗",一起共事的几位副院长和党委书记等等都几次被他"咬"过。他"咬人"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往中纪委(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递黑材料。只要你在哪件事情上与他有分歧,他就会往上边递黑材料进行政治诬陷,说你 "反对马克思主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什么的。你很难计算这些年来他用这种方式整过多少人。我又想起汤一介老先生那句话。
他也说到方克立的贪婪。那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后一次分配住宅(他费了很多唇舌给我讲解什么叫做"最后一次分配住宅"),方克立为自己挑选了那批住宅里边最好的一套,那原是给上级领导预备的。由于我不了解大陆官僚体制的隶属关系,他给我解释说,研究生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下的一个部门,职责是研究生的行政管理,研究生院院长与研究所所长是同一级别的。而方克立选中的房屋是要分配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级领导的。院领导研究不同意分配给他那套住宅,他当然要故伎重演,往中纪委递黑材料,告了好几个人,说他们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后来他又提出把原来居住在他家隔壁的住户迁走,把两套住宅打通后重新装修作为他的新住宅。院领导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同意照此办理。结果隔壁那家人原来住得好好的,必须动员他们搬迁,和他们谈条件,为他们找房子等等,麻烦透了。
郑家栋也在联络的名单里边。可是他却如人间蒸发,尝试了几个途径都联络不上。我就问起方克立和郑家栋的关系。他告诉我,我们从来没有听到郑家栋说起他和方克立之间的事情,从来没有。可是方克立在许多会议上都对郑家栋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攻击,有好几次我就在场。有时候会议的议程本来和郑家栋完全扯不上关系,可是他还是要生拉硬扯地说起郑家栋,把人家诬陷丑化一番,并且常常占用很多时间,搞得与会者都摸不着头脑,一愣一愣的。郑家栋是有成就的学者,他算什么东西?!郑家栋晋升职称申报研究课题提拔使用等等,这些本来都和方克立扯不上关系,可是他每次都要跳出来阻拦,往院领导那里也往所有相关的部门送郑家栋的黑材料,约人谈话打电话等等,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攻击。最不像话的是关于郑家栋博士生导师资格认定那件事(他又给我介绍大陆独特的"博士生导师"遴选制度)。道理上,博士生导师资格是由研究所推荐,报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会评审通过。学位委员会的行政办公室是附设在研究生院。每次哲学研究所报上来推荐增补博士生导师的名单,方克立都是直接就把郑家栋从名单上划掉了,提交到学位委员会评审的名单里就已经没有郑家栋了,你说他有多么霸道!他根本就没有这种胡作非为的权力!后来他已经从研究生院院长的位置上被免职了,郑家栋的博士生导师资格在学位委员会通过了,方克立又往中纪委递黑材料,那一次告的不仅有郑家栋,还有徐友渔/何光沪等十几个人,这些人后来统统都被取消了资格。有的学位委员跟我说,郑家栋没有资格指导博士生,天理不容!下一届博士生导师资格遴选郑家栋再一次获学位委员会通过后,方克立又上窜下跳地告状,可是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上也实在搞得过分了,所以没有人再理睬他。说到告郑家栋的黑状,这些年来方克立搞黑材料最多的就是郑家栋,没有人能够统计出他搞了多少份,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给院里各职能局的,给中纪委的,给中组部的,给国家人事部的,如果整理编排别人的黑材料也算是"学术成果",那么就是关于郑家栋一个人的黑材料方克立就已经是"著作等身"了。总是说人家"用新儒家反对马克思主义",人家是本分的学者,干吗非要用政治陷害人家?所以方克立这个人是不能够用一般的标准衡量的,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他是"属王八的,咬住人不松口"。这次郑家栋出了点事儿,方克立几次站出来大泼脏水。我问过哲学研究所的老领导,郑家栋刚调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方克立还在南开大学工作,他就往这边寄送了很多郑家栋的黑材料,以至于哲学研究所当时的党委书记和人事处长郑重其事的赴南开大学调查,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后来对于方克立的黑材料最不买账的就是哲学研究所。那些谎话方克立在不同的场合讲过数百遍,也可能他自己都分不清真假了。
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说到底这些还都属于题外话。不过和他的交谈中,我了解到方克立在担任研究生院院长期间确实长期占有研究生院招待所的一套房间,方克立后来也确实因心脏搭桥做过开胸手术,等等。最后,我才以"听说"的名义讲述了"一个女人和她的遭遇"。他告诉我,这些事情当年也有一些耳闻,可是如果当事人不站出来并且坚持到底,别人又能怎么样呢?
关于郑家栋,后来有人补充了别的资料。说是郑家栋的罪状中有两项很难赦免的,一是在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有李泽厚作序,二是当年赴台湾出席学术会议"私自拜访牟宗三"。都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方克立却始终揪住不放,每次往上边递的黑材料都要着力强调渲染一番,结果直到 2000年有关部门还要求郑家栋就这两件事儿做出"深刻的检查"。那时候,陈筠泉已经不做哲学研究所的所长了,他曾经和别人说,李泽厚作序的时候还没有发表《告别革命》,他的全国政协委员都还没有免掉,你始终揪住小郑不放,有什么道理呢?
好几位都谈到方克立和李泽厚的关系,好像都知道他们结怨。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说得具体。他说方/李本来就是两路人。方对于李的怨恨主要是下面几个原因:一是,八十年代李泽厚影响很大,汤一介等人借助"中国文化书院"也和海外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方克立虽然得到了许多现实的好处,可是学术界并不拿他当回事儿,这使得他对于李泽厚/汤一介等等由妒生恨;二是,李泽厚在境外一次演讲中说方克立是为中宣部做事儿的,这令方克立大为恼火;三是,海外有人把方克立与李泽厚比较,说方克立代表中国大陆学术界意识形态化的典型。方克立私下里说过"在学界要搞点政治,在政界要点搞学问",他认为这样就会比别人具备优势。可是他又特别忌讳学术界知道他是"玩政治的"的线人棍子打手和既得利益者。他又属于那种因为一句话就和你死缠烂打一辈子的。
1989年"六四"以后,方克立往上边递了上百份材料,其中很大部分是针对李泽厚的。他非常担心官方会遗漏掉什么,所以特别下功夫整理李泽厚在境外说了些什么,然后依照需要对那些材料加以裁减编排,并对于说话的对象场景等等也精心做了安排。这方面他是行家里手。这些材料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说李泽厚"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要着意强调李泽厚的某些理论观点与"六四"之间有内在关联;二是说李泽厚的个人生活(指男女之间)很滥,并且公然在境外宣扬 "性解放",等等。他一再敦促官方对于李泽厚之流切不可心慈手软。据说后来官方允许李泽厚去了美国,方克立颇有挫折感,他认为至少应当争取到把李泽厚监控起来,也就是国人常说的"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意思。
前不久,我去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确切地说,是去听一个研讨会。其间遇到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过来的学者,闲聊中知道他当年也是毕业于那里的研究生院,我就给了他一份印有那个专栏的《华语华人报》。第二天他告诉我报纸看过了。出乎意料的是他并没有显露出任何震惊或好奇。晚饭后我们有机会坐在一起,他说他认识某女士并且也知道她的事情。我感到很惊奇。他说:说到底,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秘密,至少不像当事人以为的那么机密。很多人都知道她们的事情。我问:"你说'她们'是什么意思?""'她们'还包括那个专栏里没有提到的另外两位。""我知道另外两位,可是她们拒绝合作。可是我以为这是一个只属于'她们'三个人的秘密。""问题就在这里,一个人的秘密是罕见的,三个人的秘密是没有的。人有一个天性,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经历的或是知道的事情说出来,不论是采取什么方式,如果他/她认为那件事情确实重要的话。她们三个人都想借着别人来述说同一件事情,相类似的遭遇,就好像那件事情只是发生在另外一个人或另外两个人身上,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是一种宣泄的方式。"我又问:"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多年,她又是身处海外,为什么说起来还是那么顾虑重重呢?"他反问道:"你理解'背景'一词的含义吗?""background?""你很小就来到北美,又是用双语写作,不大容易体会到长期生活在大洋彼岸的同胞们的感受。中西文化中的'背景'一词差异很大。在中国社会里,'背景'一词主要是指向某种权力,或者说是指向某种权力中心。同胞们说某某人'有背景'或某某事'有背景'的时候,主要是指这些人和事儿可能是和某个权力中心有关联。像方克立这种人遇到'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一类的运动,总是要抽调到中宣部使用,这种人是被认为'有背景的',是'通天的'。加上方克立不断地往高层递交什么人的黑材料,这些黑材料又总是或多或少地对于什么人发生影响,这也被认为是'有背景的'证据。在中国现代社会中,权力是无所不能的,它决定你的痛苦与欢乐,顺利与挫折,'人上人'还是'人下人',乃至决定你的生与死。和那个巨大的权力机器相比,生命个体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这使得权力具有某种魔咒的效用,令人迷信也令人恐惧。和权力相关联的'背景'也具有了某种同样的效用。而实际上,方克立也不过是做过中层官僚,他这一生都是得力于或者说是他谙熟于他的品性适合于这个体制的某些特征,其中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个体制永远欢迎揭发检举告密或诬陷者。"